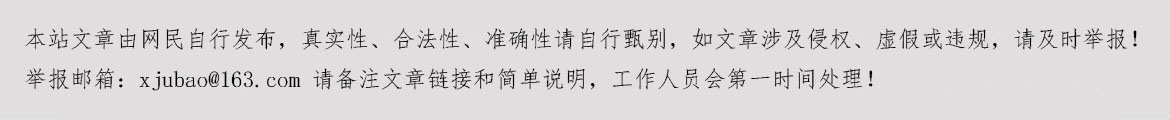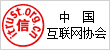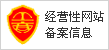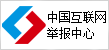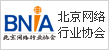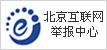2009年,“周扒皮”的后人撰文伸冤:我太姥爷不是靠剥削发家的
2021-12-23 15:05:01
电影投资 https://www.touzitop.com/
前言
图|高玉宝
1948年的一天,东北野战军四纵司令员吴克华到部队视察。
吴克华正骑着一匹枣红马一路疾驰,忽然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一个解放军战士,只见战士满头大汗,手里举着本子,一脸地为难。
“首长,你先别走,我问你几个字你再走。”
吴克华也大感诧异,就连牵马的警卫员也吃了一惊,敢有人半路拦住司令员的马,这还了得,于是急忙上前拽住战士:
“这是司令员,工作很忙,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
拦马的战士心里一紧,自己情急之下有些激动,忘了纪律了。
两人说话这个功夫,吴克华已经下了马,战士感到有些惴惴不安,以为自己会挨批评,没想到的是,吴克华并没有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问他:
“小同志,你要问什么字?”
战士脸色通红,颇有些窘态。
吴克华摸了摸战士的头时后:“哎,爱学习很好嘛。”
说着,吴克华接过战士的本子,只见上面除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大部分竟然是用图画代替的。
吴克华问了几句,才知道,战士写的原来是一个故事,心里很高兴,于是教了他几个字。
不过就连吴克华可能也没有想到,这名战士后来写的小说,对中国产生了半个多世纪的深远影响。
《半夜鸡叫》的战士作家——高玉宝
拦路的战士名叫高玉宝,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高玉宝是1927年出生于辽宁瓦房店孙家屯村人,祖籍确是在山东黄县,他的父祖一辈儿,是属于闯关东那批人,后来到东北后,逐渐生根发芽。
不过因为小的时候太穷,高玉宝15岁就给人家做长工维持生计,17岁又学了木匠。
参军一年后,高玉宝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衡宝战役,先后荣立战功六次。
不过高玉宝最出名的不是立下的赫赫战功,而是后来创作了自传体的小说《高玉宝》。
而这本小说中有一章《半夜鸡叫》,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但出乎预料的是,高玉宝参军前,基本上是个半文盲,认识的字不到一箩筐。
辽沈战役后,东野大军迅速南下,高玉宝这时萌发了创作的冲动,尤其是他想把自己个人经历,全都写到小说之中,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高玉宝想写的故事非常多,但认的字却不够,十个字中有九个字不认识,后来闹了不少笑话。
图|高玉宝年轻时
一开始,高玉宝把不会写的字用简笔画代替,如半夜鸡叫的“鸡”不会写,就直接画只鸡,杀人的“杀”不会写,高玉宝就画个人头,再在人头上画把刀。
光是“画”半夜鸡叫这一章,高玉宝就忙活了一个晚上。
尽管这样,他还是乐此不疲。
可光用图画代替也不是办法,于是高玉宝开始向周围的人请教。
很快,高玉宝拦司令员马的事儿就传遍了全军,大家都对高玉宝的创作表示了相当的支持。
一次,部队行军到湖南与江西交界地带,高玉宝从师部取回油印小报和文件后,把马拴在树上,瞥见一老汉穿着长衫马褂,举着伞走过,高玉宝一看,觉得老人是个文化人,心里一动:
“我何不向这个老人请教呢?”
高玉宝背着枪就朝老人跑过去。
图|高玉宝的入党申请书
老人没见过解放军,一看有个人扛着枪朝着他跑过来,老汉大惊失色之下,扔了雨伞就跑。
“老表、老表,你别跑啊。”
他这么一喊,老人跑得更快了,不过毕竟是年纪大了,怎么能跑得过年轻人,高玉宝很快就撵上了他,还把他的雨伞和包袱还给了他。
“老大爷,我是解放军呐。”
老汉吓得战战兢兢,话也说不利索了,高玉宝又说了一句:
“我们是替穷苦人打天下的。”
老汉这一次听懂了,于是小心地问了一句:“那你追我干什么?”
高玉宝把怀里的本子掏出来,请教老汉:“我想问您几个字?”
老汉这才恍然大悟,两人就坐在田埂上,一笔一划地练习起来,两人分手时,老汉竖起大拇指:“你们解放军,顶呱呱。”
识字的问题能解决,可高玉宝本身没接受过多少教育,什么小说的创作笔法,也一概不知,他只是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尽量客观地描述下来。
历时一年零五个月,高玉宝完成了小说的初稿。
高玉宝将完成的书稿寄送到中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科,当时文艺科科长郭永江认为小说很好,丰富且详实,唯一欠缺的就是文学性。
于是,郭永江将高玉宝调到了中南军区文化部艺术科,亲自教高玉宝修稿,改一篇,就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上发表一篇,稿子还没全发表完,就立即在全军中引发了轰动。
毛主席也从杂志上看到了高玉宝创作的小说,爱不释手,并推荐给女儿李敏、李讷看。
图|《高玉宝》
1952年8月,毛主席从周总理的口中,听说高玉宝是个“半文盲”的作家,十分高兴地说:
“好哇,好哇,共产党人真是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我要见见这位战士作家!”
这年国庆节,高玉宝收到了毛主席的邀请函,邀请他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招待会。
尽管当天出席招待会的人非常多,可毛主席还是专门打听了他坐在什么位置,端着酒杯走了过来。
“这位就是写《半夜鸡叫》的战士作家高玉宝。”
毛主席高兴地向他扬了扬杯子对他说:
“好!我们的战士作家,你的大作我已经拜读,写得好,你把剥削阶级写得很形象,来,干杯!”
值得一提的是,高玉宝参加招待会之前,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特意嘱咐,毛主席与党中央的领导人很忙,举杯庆祝的时候,不要一一碰杯,到了当天,毛主席亲自走过来敬酒,高玉宝一激动,就忘了纪律。
高玉宝事后向肖华承认错误时,肖华却没有批评他,而是羡慕地对他说:“毛主席向你敬酒,这是你的光荣,也是全军的光荣!你做得很好!”
图|《大决战》中高玉宝的形象
毛主席后来总共接见了高玉宝22次,对于高玉宝来说,也成为了他一生最值得炫耀的一件事。
高玉宝所创作的内容,大多都是来源于真实生活。
文章中塑造了一个经典的地主形象——周扒皮,从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都有很深的影响。
周扒皮也成为了地主的代名词。
因为不懂小说的创作笔法,文中用的大多数都是真人姓名,如小说的主人公就叫高玉宝,而地主的名字周扒皮也是确有其人。
“周扒皮”的名字叫周春富。
“半夜鸡叫是真实的吗?”
高玉宝笔下的周扒皮凶残狠毒,和同样是解放战争时期经典地主形象南霸天、黄世仁有得一比。
晚年的高玉宝在回忆起小说创作时的经历,还曾谈到过给地主家里当猪倌时候的经历:
“我给周扒皮当猪倌,力没少出,气没少受,还挨了多次打。但是,也算开了眼界。我觉得,周扒皮‘土’是‘土’了点,连多送几个孩子读书都舍不得,也不善待儿子和媳妇,对待长工尤其苛刻。还喜欢偷偷摸摸的。但是,他这个人很精明,很会动脑筋,很勤快,也很会管理。他要学鸡叫,就得比长工还要起得早吧?!实际上,他不是靠勤劳致富,靠剥削发家。
时隔多年后,我们看到《半夜鸡叫》这篇文章时,仍然会为高玉宝智斗地主感到好笑时,却不免产生另外一个疑惑。
“周扒皮”这个人究竟存不存在?他的命运后来又如何了呢?
2005年,大连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孟令骞买了一本《高玉宝续集》再版,他拿着书到高玉宝家中采访。并将采访以文字的形式发表。
孟令骞还有一个身份——他喊“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为太姥爷。
孟令骞见高玉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半夜鸡叫是真的吗?”
高玉宝的回答是:
“当然是真的,当时我们村四个地主都半夜学鸡叫,只不过后来发表和出书后,都写到周扒皮一个人身上去了。”
孟令骞又问:
“《高玉宝》是小说,为什么要把反面人物用真实姓名写进去?有考虑过对他们的子女后代产生影响吗?”
听到这个问题,高玉宝沉默了一阵,最后坦白地说了一句:
“这个我没想过,我那时不懂什么叫小说,发表了五六篇后,才知道小说不能写真实姓名……”
两人的采访很简单,一直到最后,孟令骞也没承认,自己就是小说周扒皮原型的曾外孙。
尽管如此,有关“半夜鸡叫”的故事,孟令骞认为没有。
从农学、动物学的角度上讲,“半夜鸡叫”很不合常理,即便是干活,大半夜的漆黑一片,又能干得了什么活
同为黄店屯村的孔庆祥也回忆称:
“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他地方就没有。”
需要指出的是,高玉宝的小说创作,来源大多都是属于真实的,但因为他当时不懂小说的创作,于是在修改时采纳了不少中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科科长郭永江的建议。
高玉宝一开始写小说,文章里就是写的老家大连瓦房店4个地主,后来是郭永江建议他:
“要写重点,抓典型,把这四个地主的事件和特征叠加在一起,写成一个人。”
图|《高玉宝》书中一节《我要读书》
郭永祥后来还建议,小说中地主形象既然已经浓缩成一个人,那么就不该再是生活中的那一个人,应该另外取一个名字。
但高玉宝并不懂这一点,于是沿用了周春富的名字。
这才有了后来经典的周扒皮形象。
时隔多年后,孟令骞还曾披露过,有关小说的著作权一事引起过争执,郭永江认为,小说是他创作的,依据来源就是高玉宝的生平经历,晚年还交代子女,要把小说的著作权要回来。
站在比较公立的角度上看待这件事的话,高玉宝与郭永祥一开始在创作过程中,就存在沟通的问题。
高玉宝所写的文字,从他的角度上来看待,是属于纪实文学,小说反映的本来就是真人真事,而郭永祥提供的则是小说的描述方式,更改了故事中真实的一面,加入了艺术创作。削弱了原版纪实的味道。
周扒皮真是个老实厚道的人?
2009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孟令骞的文章《半夜鸡不叫》。
孟令骞在文中为太姥爷辩护:
“我太姥爷周春富不是靠剥削发家的。”
孟令骞认为,高玉宝在小说中把周春富写得太恶劣,描得“太恶劣”,以至于遭到了后来的厄运。
事实上周春富死于1949年,而高玉宝的小说则是在1951年前后发表的,正式发表就要到1955年4月。两者之间不太可能有关系。
周春富的悲剧,其实是时代的悲剧,尽管有人反映周春富并不像是小说中表现的那么恶,但从根上也算是地主。
黄店屯的农民闫振民晚年回忆称:
“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
历史上闯关东大致时间是在清末,孟令骞也觉得他太姥爷应该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
图|七十年代时期,高玉宝在孩子们中间
东北这片土地上,有清一代一直是地广人稀,早在清初的时候,便招募民众到东北垦荒,当时从各地前往东北的民众,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垦殖土地。
周春富也是当时东北垦荒中为数不多勤恳务实的农民之一。
当然也源于东北常年地广人稀,关外的人地关系,远远不像是关内那么紧张,基本上大多都有自己的土地,只有少部分是依靠租地生活,也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地可供他们垦荒。
有关周春富有多少的?在各种各样的资料里,记载是不一样的。
有的资料说,周春富有耕地一百多亩,也有的说有两三百亩,据一些曾和周春富打过交道的老人说,周春富拥有耕地40天(大约2413亩土地)。
可即便是这样,周春富在当地依旧只是一个小地主,据闫振民回忆说:
“当时复县(瓦房店市)有一大地主陈维礼家里有地7200多亩,周春富所拥有的尚不及陈维礼一个零头。”
除了土地外,周春富还有染坊、油坊、小卖店等产业。
“方圆20里,就这一家小卖店,他二儿子在外经商,很有能耐。在村里算不上是最有钱的,但很不错。”
需要指出的是,闫振民家本身也有地50余亩,他自己不仅种地,有时也在周春富家打短工,后来解放后,被划为中农。
图|《高玉宝续集》
闫振民回忆周春富时曾称:
“他们家的房子还不如自己家的好,周春富平日里不看重吃穿,最看重土地。一有钱就买地,而自己家的房子却很差。”
许多村民也对此记忆犹新:
“他的房子不好,现在的(周春富旧居)是翻新过的。他省钱就奔着买地,自己家开油坊,有豆油,但不舍得多用,过年节时油都放得少。”
另外也许是勤俭持家有些过了头,周春富对家里人确实是有些苛待,有人回忆称,周春富家里四个儿媳被他逼着干活。
“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时间过去60多年以后,曾经在周春富家里当长工的王义帧回忆称:
“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活。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周春富年轻时和大多数人一样,下地干活,夏天身上不爱穿衣服,太阳晒得紫黑一片,只是后来年纪大了,才不下地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也会和他的父祖辈儿一样,晚年在老家是含饴弄孙。
高玉宝晚年接受采访时,曾被问及周春富是否真有其人。
图|高玉宝
高老很明确地回答:“周扒皮是个有血案的恶霸地主。他的确是在被批斗时,被愤怒的土改群众活活打死的。他干的坏事、丑事比我在书中写的要多得多。我是给他留足了面子的。“
不过随后,高老话锋一转,又接着说道: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土改那时,在执行政策方面,也并不是在全国所有的地方、也不是在对待所有人的问题上都没有出一点偏差、没有一点错误。也不光土改是这样,我国的任何一个运动都概不例外。至于周扒皮,究竟该划定什么成分、该不该平反或正名,讨论似乎意义不大。因为,他的子孙后代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他背上什么‘包袱’。”
令高玉宝最为歉疚的一件事是,当初在改成这种不伦不类的“自传体小说”后,就不该再用真名,比如周扒皮,再比如他本人。
从高玉宝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他一开始所写的故事,或许是确有其事,但后来经过艺术化的加工后,却显得有些失真,在那个年代里,这些失真的东西,被当作真实发生的故事,以至于代代传承。
图|高玉宝晚年书法
正如解放时期的艺术创作,所谓南霸天根据考证,并无其人其事。黄世仁这个典型的地主形象,也是艺术创作出来的。
正因为周扒皮的形象过于经典,成为了那个时代下,人们所痛恨的旧社会的一个代表。
周春富的遭遇,也只是那个特殊时代下的缩影,若说他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大善人,那么我是不相信的,但如果说他就是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也是有失偏颇的。